作为张艺谋的早期电影代表作之一,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摘取了诸多奖项。它以苏童的小说《妻妾成群》为蓝本,讲述了民国年间的大户人家里女性的悲剧故事。
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,有所改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,张艺谋的这部电影最大的改动便是在于“将原作小说中氤氲着雾气的江南背景更改为凄艳壮烈的陕西院落”,这一改动乍看有种江南水乡秒变黄土高坡的意味,但重点实际上在于“院落”,所谓“深闺大院”,就是将空间格局限制住了,有了一定范围,比起如诗如画的“陈家花园”,四四方方棺材般的北方院子更容易在视觉上带给观众以“束缚”之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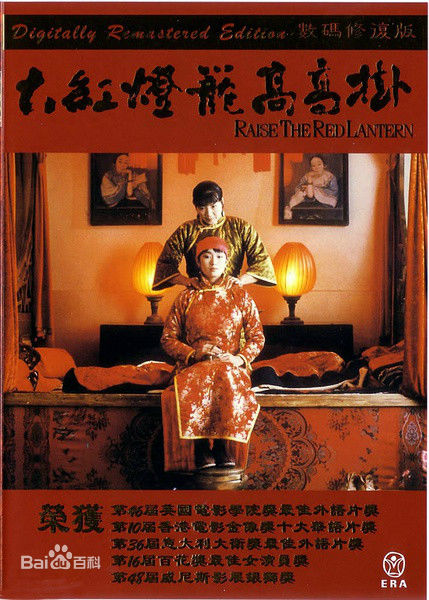
除此之外,电影在其他方面也显示出与原著的不同——
一、主要意象的变化。根据资料,“为了符合影像化呈现,张艺谋在影片中自创了点灯、封灯等一系列关于灯的仪式”,再结合影片内容,可知导演设置的主要意象之一是“大红灯笼”了,陈佐千的四房太太是否受宠,全反映在灯笼上,“受宠便红”,而她们争宠也是围绕“点灯”一事,因着一人多点了几天灯,或是点了“长明灯”,便要有人急躁、忌恨,生出事端来;大红色的灯笼高高挂在乌黑的屋檐下,白森森的雪中,这种颜色的反差正引人注目,象征了陈佐千权力至高,从而引诱着牢笼中的妻妾互相争夺残杀。
在原著里,频繁出现的一个意象是“井”“井水”:“井水是蓝黑色的,水面上也浮着陈年的落叶,颂莲看见自己的脸在水中闪烁不定,听见自己的喘息声被吸入井中放大了,沉闷而微弱”“她看见叶子像一片饰物浮在幽蓝的死水之上,把她的浮影遮盖了一块,她竟然看不见自己的眼睛”“她想返身逃走,但整个身体好像被牢牢地吸附在井台上,欲罢不能”……每当颂莲的内心感到不安,作者都会将笔锋转到井上进行描写,以一口“死人井”渲染凄惨恐怖的氛围,以水面映射颂莲的变化,或是变得困惑,或是变得庸俗,或是变得急功近利。
原著里的井绝对代表着“不祥之物”,颂莲却还总会时不时地停留于此,这既暗示了她的悲剧,亦暗示了其他女人的悲剧。梅姗与高医生私通被发现后,深更半夜被抬到井边扔了下去,颂莲因见证了杀人的过程而变疯,“有时候绕着废井一圈一圈地转,对着井中说话”“我不跳,我不跳,她说她不跳井”。
“井”的意象放在南方背景下是特殊而普遍的,在电影中则被拆分成“镜子”和“屋子”两个意象。颂莲在新婚之夜举灯对镜,审视着不堪而卑微的自己;在落寞的时候,她常常走上屋顶,不远处还有一个“死人屋”,前代姨太太以及梅姗就是被关在屋子里上吊处死的。
二、加强了颂莲的原生性格。由于播放时间所限,电影往往需要在短时间内使观众对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产生深刻印象。“四太太颂莲被抬进陈家花园时候是十九岁,她是傍晚时分由四个乡下轿夫抬进花园西侧后门的。仆人们正在井边洗旧毛线,看见那顶轿子悄悄地从月亮门里挤进来,下来一个白衣黑裙的女学生。仆人们以为是在北平读书的大小姐回家了,迎上去一看不是,是一个满脸尘土疲惫不堪的女学生。”原文开头叙述背景娓娓道来,主要表现颂莲身份地位处于下风的状态;电影则讲述颂莲与轿子相错,独身一人走到陈家大院,显示骨子里的坚强特质,强调了她作为一个“洋学生”的高傲、与众不同,同中后期沦落妾室争斗而迷失了自我形成反差。电影越是强调过颂莲的原生性格,也就越显得其结局可悲。
三、感情线的隐晦。原著里各人物之间的关系并非错综复杂,影片将其中的3条感情线处理得比较隐晦:
第一条作为小说中的插叙藏在陈佐千的回忆里。“陈佐千第一次去看颂莲。颂莲闭门不见,从门里扔出一句话,去西餐社见面……颂莲打着一顶细花绸伞姗姗而来,陈佐千就开心地笑了。”电影将陈佐千设置为一个从头到尾不露面的男人,神秘感与威慑力兼具,少见情感交流,而小说由于常见细节描写,比如陈佐千与颂莲第一次见面的情景,比如陈佐千误会烧后窘迫地搓着手来回走的行为,看起来显得其更有血有肉一些;但实际上,所谓“有血有肉”不过是假象,这体现在陈佐千对于性的追求上,“陈佐千更迷恋的是颂莲在床上的热情和机敏。他似乎在初遇颂莲的时候就看见了销魂种种,以后果然被证实。”他娶颂莲,并不是因为有感情,而是出于满足性欲的目的,体现了强权之男权物化女性,而随着陈佐千被“掏空”,妾室被“闲置”,只会导致两种悲剧,一种是被迫贞洁禁欲的女人们等待老死,一种是红杏出墙东窗事发后被杀死。电影省去小说中的细节,便于使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一夫多妻制下的悲剧性。
第二条是飞浦与颂莲的禁忌之恋。颂莲与大太太的矛盾,与其儿子飞浦有一定的关系。飞浦之于颂莲,是一种明争暗斗过后的一丝安慰和依恋;颂莲之于飞浦,是一种特殊的存在,倒不一定是爱。颂莲失宠后度日如年,连过生日也只能喝酒消愁,这时候飞浦前来探望她,两人到动情处有些不自禁,但却以飞浦的软弱终结,“颂莲我喜欢你,我不骗你。颂莲说,你喜欢我却这样待我。”小说讲述的他们是两情相悦的,电影里交代得就比较隐晦,甚至有点像颂莲的单相思,她拒绝了原本是别人送给飞浦的荷包,气恼他的欺骗,令他出去后开始发酒疯,感情线就此戛然而止;电影将这部分情节剪得很利落,少了些暧昧戏,并安排颂莲失口说出三太太梅姗偷情的事实导致了“间接杀人”,成为了使她精神错乱的原因之一。
第三条是飞浦与顾少爷的断袖情。飞浦拒绝颂莲的情意是因为他“害怕女人”,依据小说给出的信息,可知在封建大家庭生活的长子飞浦是个很特别的男人,他不好女色,甚至对女人有着生理性恐惧,做生意赔个精光,喜欢游玩。由于对女人的抗拒,他更与顾少爷有着确实的私情:“看你们两个多要好,颂莲抿着嘴笑道我还没见过两个大男人手拉手走路呢。飞浦的样子有点窘,他说,我们从小就认识,在一个学堂念书的。再看顾家少爷,更是脸红红的。”“他跟那个顾少爷怎么那样好?陈佐千笑了一声,说,那有什么奇怪的,男人与男人之间有些事你不懂的。”在顾少爷未出场的情况下,“断袖情”在电影中也无反映。
在感情线上,“箫”(电影中是笛子)作为一件乐器起到的是传情达意的作用,亦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感情。很明显的几个地方在于:陈佐千因怀疑箫的来路便烧了,颂莲因听到飞浦吹箫便渐渐喜欢上了他,之后颂莲学习吹箫却未果。主人公一直与这件乐器存在着联系却没能维系,暗示了最后的悲剧。
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,高挂的是传统的婚姻制度,低落的是女人应有的地位,。电影讲述的故事处处强调“规矩”二字,处处显示出这样一个可悲的逻辑:女人=东西≠人,如颂莲所说的:“女人到底算个什么东西,就像狗、像猫、像金鱼、像老鼠,什么都像,就是不像人。”处于如此地位上的女人们,无论属于北还是南,都逃不过互相争斗和绞杀的命运。